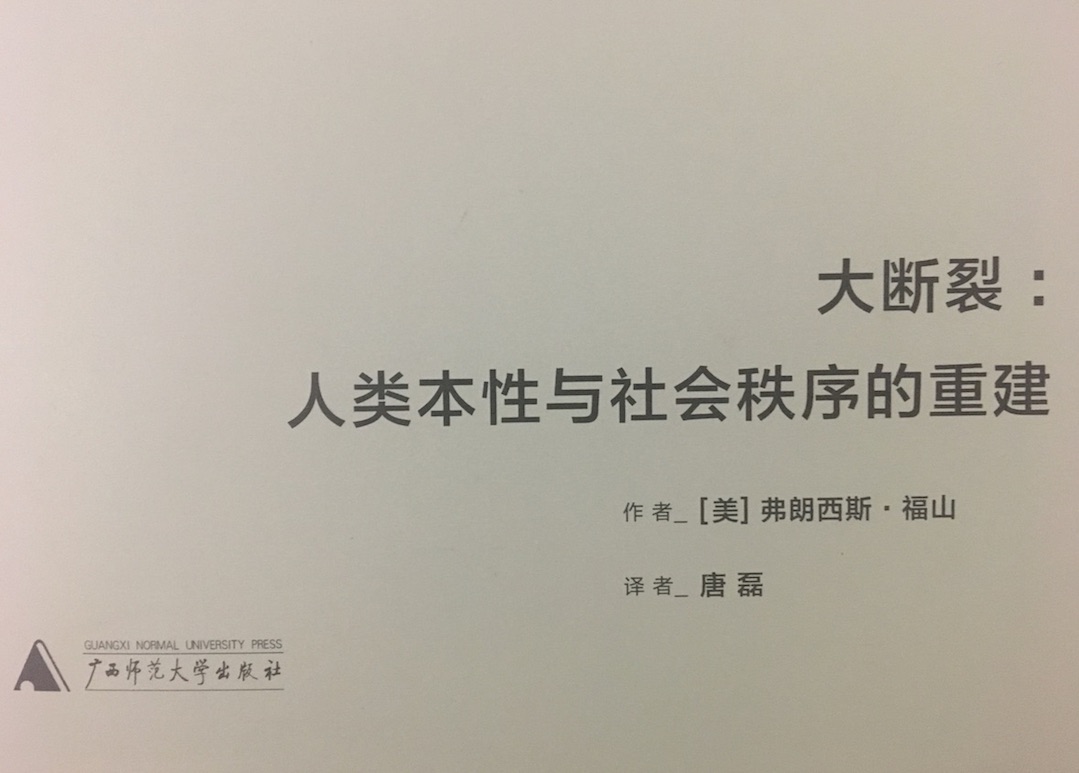
弗朗西斯·福山生于1952年10月27日,是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为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Olivier Nomellini高级研究员,他还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有多项学术荣誉及成就。福山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
福山有其一套国际政治经济思想体系,又称为福山主义。世人对福山主义有不同的评价与观点,但在福山写过的诸多著作中,有一本写于1999年名为《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却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讨论信息技术变革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其著作中难得讨论技术的著作。
在福山这本1999年的《大断裂──人性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他从人性的角度观察了信息技术变革给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重大改变,包括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模式以及组织方式——旧有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冲击,福山将此种种归为“社会资本”的大断裂。
“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最早是1916年由Lyda Judson Hanifan提出。福山将之定义为“一套为某一群体成员共享并能使其形成合作的非正式的价值和规范”。福山进一步解释:如果群体中的成员希望其他成员的所作所为诚实可靠,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信任就像润滑剂一样,帮助集体和组织的运转更加高效。
福山认为任何社会都有社会资本,区别在于所谓“信任半径”,即类似诚实和互惠这样的合作性社会准则在一定限度的人群范围内共享,并且拒斥与同一社会中该群体以外的其他人的共享。当然,社会的协调运行也可以依赖契约、法律体系等,但非正式规范可以大幅减少所谓的交易成本,即对契约进行监督、缔结、调整和强制执行等的费用。
《大断裂》一书中文版的序言作者刘瑜把“社会资本”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密度与黏性。根据有关的“社会资本”理论,人们通过密集、广泛的社会交往培养参与精神、组织能力、责任意识、契约习惯乃至信任。“社会资本”被认为是西方繁荣发展的秘密,但《大断裂》认为1999年的西方出现个人主义盛行、社群主义衰退,导致西方的“社会资本”正在大规模流失。
在另一方面,福山认为互联网兴起之后,一种新的非正式的、松散的、水平的社会交往正在崛起,人们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结社”。某种意义上,垂直型社团的减少以及水平型社团的增加,这样的结果是“社会资本”转型了。
在福山看来,个人主义不断膨胀造成了传统权威和社会规范不同程度的消解,但基于个体理性和竞争关系自发产生的互惠利他合作关系,仍然是形成各种形式社会联结和社会资本的基石。在新技术条件下,社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促成了社会网络的兴起,使得社会资本对于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更大。大断裂不可避免,但社会规范的重建也始终可期。
福山在1999年对于信息技术变革的社会影响的思考,对于今天正在发生的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之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很有参考价值。
以下文字摘录自《大断裂──人性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的第12章“技术、网络与社会资本”
马克斯·韦伯认为,以官僚制表现出来的理性的、等级制的权威是现代性的核心所在。然而,我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现则是, 官僚等级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出现衰落,正被更加非正式的、自组织的协作形式所取代。
公司的等级制也遭受了冲击。大型的、等级过度森严的公司出现了大幅衰退——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就是典型的例子——成了规模更小、反应更敏捷、更具灵活性的竞争者的牺牲品。商学院教授、企业经营顾问和信息技术专家都曾着重指出过高度分权管理的公司的优点,其中还有人称,在21世纪,大型的、等级制的公司将彻底被新的组织形式即网络所取代。
权力集中的、专制的公司走向衰落的原因:它们无力应对所置身的日益复杂的世界对信息的需求。恰在全球社会经历从工业生产方式向高科技和以信息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之际,等级制遭遇危机,这不是一个偶然。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并且经济活动变得更加复杂, 实现统治所需要的信息以几何指数增长。现代治理需要专门的技术,这些知识不可能尽为统治者所掌握,因此他必须事事依赖技术专家,从武器设计到财政管理。并且,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其绝大部分实际上都只在产生的当地局部流转。假如有供应商提供质量低劣的铆钉,能知道此事的多半是铆工,而不是集中规划部门里的经济事物官员或公司管理层中的副总级人物。
但是,将权力下放到技术专家或这些创造并运用地方性知识 (local knowledge)的人手里,就会削弱独裁者的权力。
这些老总,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创立公司的老总,往往想控制公司内部的一切事务,把雇员当做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人来对待。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他们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这种决策方式就变得过于呆板,老板反而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人。
企业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指出,公司在组织内部向下放权的现象在过去至少一百年里持续发生。像通用汽车和杜邦化学这类大型多部门制公司实行等级制架构,但与小型家庭企业相比,它们在经营权分散化方面程度还是较高。这些困扰大型等级制组织的问题绝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有理由相信,在其内部权力下放的过程仍将继续。但新的问题也随即而来:在一个权力分散的、基层员工获得新近授权的组织内如何协调各方的行动。
解决途径之一是市场,让彼此平等的买卖双方在没有中央权力控制的情况下自主达成有效的结果。美国商业界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外包热潮就是市场关系取代等级制管控的一种表现。但市场交换会产生交易成本,没有一家公司会按照人人相互竞争的市场形式组织其核心部门。
对高度分散的组织进行协调的另一种渠道是网络,它不是由中央集权的权威缔造,而是由权力分散的各行动者通过互动形成某种自发秩序。如果网络真能产生秩序,则它们必须依靠在正式组织中形成的非正式规范,也就是社会资本。
有大量文献研究了作为传统的市场和等级制组织中介形式的市场是如何兴起的,人们认为网络比大型等级制组织更能适应技术的发展。托马斯·马隆(Thomas Malone)和琼安·耶玆(Joanne Yates)认为,廉价的、泛在的信息技术能降低因发生市场关系而产生的交易成本,从而减少人们创建等级管理体制的积极性。许多热心鼓吹信息革命的人不仅把新兴的互联网视为一种有用的新型通讯技术,还认为它的出现预示着一种全新的、非等级制的组织形式,唯独这样形式的组织才能适用复杂的、信息密集的经济世界的需求。
典型的等级制组织呈金字塔形,扁平化后的组织仍保持着集权性和等级性,改变的只是介于顶层和底层之间的管理等级的数量减少了。扁平化组织(flat organizations)能带来控制范围的扩大;如果施行得当,高层管理人员就不会为承担具体的管理责任而叫苦连天,而是把权力下放到组织的下级部门。
如果我们不将网络视为某种类型的正式组织,而是视为社会资本,就会更好地理解网络的经济功能究竟体现在何处。按照下述观点,网络是一种关于信任的道德关系:网络是由一群个体行为者组成的,他们分享着超越普通的市场交易所需的非正式规范和价值观。
对网络的这一定义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网络与市场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由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来定义的。这意味着,网络内部经济交换活动的进行与市场中的经济交易相比,有一个不同的基础。
另一方面,网络不同于等级制的地方在于前者基于共享的非正式规范而不是正式的职权关系(authority relationships)。在此意义上,网络可以与正式的等级制共存。
那种正式的等级制很快可能消失的说法十分值得怀疑。网络正变得日益重要,从而会与正式的等级制共存。但为什么非正式的网络就不会与之共灭呢?答案之一涉及在经济活动日益复杂的情况下通过等级制实现协调的问题。
等级制组织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可以从信息在其中流通的方式上获得理解。在制造公司里,等级制的存在是为了协调生产过程中物资的流动。物资流动是由正式的权力架构来决定的,但信息的流通有一套相当不同的方式。信息是一种特殊的价值物(商品)。制造出信息可能是极其困难而且昂贵的,而一旦信息产生,进一步复制它却是几乎免费的。数字时代更是如此,鼠标一击可以产生一份计算机文件的无穷副本。
因此,尽管在组织整体利益层面需要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但允许如此则会与等级制内部不同人的个体利益相冲突。常言说,信息就是权力,组织内的不同个体会将授让还是扣留信息作为尽可能提升自己相对权力的重要手段。每一个在等级制组织中工作的人都清楚,上下级之间或相互竞争的部门之间,始终都存在为了控制信息而进行的斗争。
网络(定义为共享非正式规范和价值观的群体)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为信息在组织内外的流通提供了其他的渠道。
理想中的企业文化同时给个体员工提供一个群体和一个个体身份,鼓励他们为群体目标而努力,而群体目标又在此促进组织内部的信息流通。
社会资本对于管理那些运用复杂而难以理解、隐性和难以传播的知识的高技能人才也十分重要。
大多数软件工程师远比管理他们的人要熟悉本职工作;他们自己就能对自己的生产率做出有根据的判断。这样的员工通常被认为能按照内化于己身的专业标准来进行自我管理。
以亨利·福特的巨型工厂为代表的20世纪早期的工作场所, 是一个以高度规章化、程式化为特点的等级制组织。在这里,由一个集权的、官僚化的等级体制来确立和控制细致的劳动分工,该体制还设定了大量正式规则来约束组织内的个体成员应如何行事。福特所施行的科学管理原则,是由工业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的。它包含一个隐形的前提,即管理情报(managerial intelligence)有一个规模效益的问题,如果情报被限定在白领管理层流通而不是分发给整个组织,可能组织的运作效率更高。
泰勒制是协调低技能产业工人活动的有效手段——也许是唯一的手段。在20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中,有半数福特公司的蓝领工人是那些不会讲英语的第一代移民,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80% 的蓝领工人没有高中学历。
但泰勒制随即遇到了大型等级制组织的所有问题,包括决策过程缓慢,工作规则死板,适应新环境能力低下等等。从等级制的、泰勒式的组织演变为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需要卸除正式的、官僚化的规则的协调功能,将之转授给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在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内,权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某种允许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方式内化于组织之中。
—个精益化的或及时生产制(just-in-time)的汽车制造厂就是扁平的、后福特式组织。就正式权威问题来说,原先指定给白领的中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如今被蓝领的流水线工人自己以团队形式来承担。每天的生产计划、机器安装、工作纪律和质量控制,全由工厂最底层的劳动力来掌握和处理。
正如许多研究成果所示,精益化生产以创造大量利润为标志, 提高了汽车业的生产力,同时也提升了产品质量。其原因在于,处理地方性信息的活动能更接近于产生它的地方:如果分包商提供的车门不合用,负责将它安装到车身上的工人就既有权力又有动力来确保该问题得到解决,而不是让相关信息在冗长的管理层次体系中来回传递最后不知所终。
社会资本对于实现一个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的重要性,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
萨克森奈恩在比较了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的不同表现后指出,硅谷成功的一条重要原因在于当地独特的文化。萨克森奈恩清楚地揭示出,在硅谷表面看上去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竞争背后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网络,它们将不同公司(从半导体业到个人计算机业)的个体联结起来。这些社会网络有各自不同的根源,包括共同的教育背景(例如都在伯克利或斯坦福获得电子工程学位)和共同的就业经历(许多半导体产业的关键性人物都曾共事过,如罗伯特·伊斯和安迪·葛洛夫在该产业发展初期都在仙童半导体公司工作),或是在其成长过程中受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旧金山)湾区反主流文化潮流所倡导的那些规范的洗礼。
“当地工程师认识到,他们通过网络获取的反馈和信息的质量,取决于信息提供者的可靠度或者说可信度。只有那些与你有着共同背景和工作经历的人才能确保这种质量。”因此,这些共享的职业和个人规范构成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
由这类非正式网络造就的社会资本令硅谷得以在研发上形成规模效益,而大型的垂直整合的公司则做不到这一点。有不少文献谈到过日本公司的合作特点以及“经连会”(Keiretsu)组织成员彼此分享技术的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整个硅谷可以被视作一个大型的网络组织,它在汲取组织内部专家知识和专门技能上的表现,即使最大的、垂直整合的日本电子科技公司及其经连会合作伙伴也无法做到。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等评论者曾指出,虽然有通信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但许多产业,特别是高科技研发产业,依然集中于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假如信息能通过电子网络被轻易分享,为何没有出现产业地理分布的进一步离散化呢?
因此,尽管货物一类产品的生产可以分包给世界上劳动力成本低的其他地方,但精密的技术开发活动要想做到这—点就困难得多。
弱”联结仍然重要;想让创意和创新能自由流动,就需要网络彼此交叠。另一方面,没有社会联结,创意就很难转化为财富,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有了宽带和高速的网络连通,但社会联结仍然需要其他一些东西。

